古人云,十年磨一剑;我却是,十年谋一问:屈原放逐陵阳做铜官吗?
首先,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这在《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里有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左徒”是周朝楚国特有的官名,中原诸侯国无。除屈原在楚怀王时曾经担任过左徒一职外,后来的春申君也担任过左徒一职。如《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里有记载:“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馀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对于“左徒”的职掌及官阶等情况,从《史记》关于屈原、春申君担任左徒一职的记载内容来看,也能有个大概的了解。至少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可为参照。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左徒,是楚国特有的官,或者说是专为屈原、春申君特设的官职,入内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出则接待宾客。有人说,“左徒”相当于左丞相,仅次于令尹,可以议论国政,主管外交。甚至有学者形象的说,屈原在楚怀王时期任左徒,这个官职,有点像新中国早期的政务院总理,也有点像美国国务卿的那个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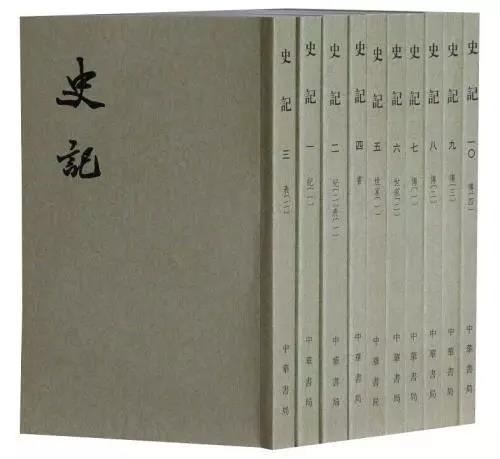
△司马迁《史记》 资料图片
其次,屈原使于齐的时候不在“左徒”职位上。《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里提及屈原,这一点很重要。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从屈原与楚怀王的对话中,既看到屈原在楚怀王时期议论国政的情况,又看到屈原与张仪之间的关系如何了。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里说:“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也说,周赧王五年,即公元前310年,辛亥,“张仪相魏一岁,卒。”也就是说,张仪逝世的那年,屈原31岁。屈原任左徒这个职务的时候,年龄较轻。更重要的是,《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里,详细记载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后议论国政的情况:“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里也指出:“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请大家注意这里的说明:“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说明屈原使于齐的时候,已经不在“左徒”的职位上,是以什么身份使于齐,是值得研究的。
第三,屈原是在楚怀王与楚顷襄王交替之际被称为“三闾大夫”的。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交待的非常清楚:“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三闾大夫”是战国时楚国为屈原特设的官职。在《史记》屈原列传的裴骃集解中,骃案《离骚序》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有的学者认为,“三闾大夫”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昭、屈、景三大姓子弟教育等宗教事务的官;有的学者认为,“左徒”与“三闾大夫”可能是同一职官;有的学者认为,“三闾大夫”可能是“左徒”的属官;有的学者认为,“三闾大夫”可能就是楚宫中的“莫敖”等等,对于这些说法,都很难得到证实。
第四,屈原放逐陵阳做铜官考。
一是《哀郢》的“陵阳”作地名解。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的结束语:“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直接提到的屈原四篇著作,最后一篇是《哀郢》。《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大概是《哀郢》的创作地点、时间的内证和判断依据。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辛已,他是属蛇的。周显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334年,屈原7岁的时候,安徽的池州、陵阳地区,就已经楚灭越。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记载:“越王无疆伐齐。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明嘉靖《池州府志》卷一,也有相关内容的记载。公元前323年,即楚怀王6年,屈原18岁,是年楚制《鄂君启节》,舟节的路线到陵阳。在公元前287年,楚顷襄王12年,屈原约54岁,始放逐陵阳做铜官。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21年,屈原约63岁,“于是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如何理解《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哀郢》作于屈原放逐之中,是毫无争议的;《哀郢》反映的地名方位,尽管有不同的看法,《哀郢》作于长江而不是汉北,也是毫无争议的。洪兴祖《楚辞补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汤炳正《楚辞今注》等认为,《哀郢》中的“陵阳”,应作地名解,即今安徽青阳县南的“陵阳镇”一带。今日池州的九华山,即古称九子山、陵阳山,已经成为共识。屈原不仅到过陵阳,而且在陵阳生活、工作了九年,也渐渐地成为人们的共识。尤其是楚灭越后,夺取了扬越青铜矿产和冶练基地,使“陵阳之金”“丹阳善铜”和铜绿山的青铜,源源不断地流通到楚国都城和其它城市,从而使楚国军事力量迅速强大,经济发展迅猛。
二是贵池东周铜锭的分析很重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刊登的张敬国、李仲达、华觉明《贵池东周铜锭的分析研究——中国始用硫化矿炼铜的一个线索》一文,对我开展屈原放逐陵阳做铜官的考证,有很大的启发。该文认为,早期炼铜技术的研究,对于阐明先秦物质文化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就现有资料来看,伊朗、两河流域和欧洲一些地区掌握炼铜技术较早,硫化矿的使用也先于中国。如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在公元前约1200年已用硫化矿炼铜。中国什么时候开始用硫化矿炼铜,是冶铸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铜矿预焙烧迟至宋代才见于文献记载,早期铜器分析又未能提供使用硫化矿的确证,曾经设想硫化矿较晚(例如东汉)才被使用。但是,1977年8月,在安徽省贵池县里山公社齐山大队老十队徽家冲(今安徽省池州市平天湖管委会清溪街道办事区齐山社居老十队徽家冲)青铜窑藏发现铜锭7件,青铜器有斧、铲、鎒、蚌镰、鱼钩、锯、矛、剑、刀、鼎、盘、杯等约共50件,从器形和铭文看,初步判断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遗物。从贵池齐山铜锭的检验来看,早自春秋晚期已使用硫化矿炼铜是有可能的。贵池齐山徽家冲窑藏铜锭的出土,把我国硫化矿炼铜这一冶铜术使用的时间,上溯了一千多年。特别是众多的青铜农具在两淮流域,还是第一次发现。循此追索,必能为阐明古淮夷冶铜术的发生、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提供更多的社会信息与工艺信息。贵池是历史著名的矿冶产地,位于《禹贡》所载盛产金锡的“扬州”境内。北周庚信《枯树赋》中有“南陵以梅根作冶”,东晋时的梅根冶,唐孟浩然诗中“火炽梅根冶”句。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其第十四首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李白的诗句,生动描绘了贵池金属冶炼业的盛况。尤其是在贵池齐山徽家冲青铜窑附近,就是安徽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七星墩遗址”:王家墩、汪家墩、潘家墩、叶家墩、孙家墩、月形墩、虎形墩,地方特征较明显。

△大工山——凤凰山铜矿遗址 资料图片
三是铜陵的铜官山与屈原做铜官关系密切。在历史上,铜陵隶属陵阳、池州等,详见沿革。丹阳,郡名。《汉书·地理志》作“丹扬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改鄣郡为丹扬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汉代,在丹扬郡专设铜官,与屈原在陵阳做铜官有关,这是全国唯一,也是楚国特有的现象。屈原是“三闾大夫”,“三闾大夫”也是楚国特设的官职,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贵族昭、屈、景三姓教育的闲差;尽管屈原被疏,远离郢都,但他与楚王近亲,比外人强,放逐陵阳,兼管青铜这一战略物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关于设铜官的事,正史是有记载的,如《汉书·地理志》:“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一。有铜官。”大家知道,铜陵产铜久负盛名,先秦时期就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产铜基地,文献史料屡有记载,其铜矿采冶活动最早可上溯到商代,一直延至当代,3000余年,久盛不衰,绵延不断。西汉唯一的“铜官”,六朝著名的“梅梗冶”,唐、宋时期的“铜官场”、“利国监”等官方重要的采冶机构,均设置于此,世称“中国古铜都”。铜陵古代铜矿遗址,大多分布在铜官山、狮子山、凤凰山等几个铜矿区周围,基本包括境内东南大部分的丘陵地带。其中属于先秦时期的矿冶遗址,就有木鱼山、万迎山、药园山、金山等处。铜陵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约占整个皖南地区1/4还多。这些铜器,大体可分为生活用具、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四类。年代上,分为商至西周、春秋前期、春秋后期至战国三个历史阶段。文化面貌上,既有与中原青铜文化相同的因素,又有吴越铜器所特有的南方风格,还有一些则反映出强烈的皖南土著文化色彩。铜陵出土的春秋晚期铜器,还有不少地方与楚器相似,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尤其1998年在铜陵狮子山区西湖镇朝山村出土的6件春秋人面形铜饰件,应是祭祀用的神器,在整个皖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这对研究屈原《天问》是有益的。铜陵市,以铜立市;铜陵有色公司,以铜立企业;铜陵人,注意研究铜官与屈原,也是有益的。
四是《盐铁论》的“陵阳之金”是铜陵立市之名。2017年11月,黄山书社出版了我编著的《陵阳文史探微》,那是一本资料性的著作。在该书的第三部分第4节里,专门提到《盐铁论·通有》“左陵阳之金”。该文的注释,引自王利器《盐铁论校注》通有第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所谓“左”,古代言地望,常常拿“左”“右”来指定其方位,这是把当时首都作为坐标而言的。由于中国古代首都,一般都在北方,因之,所谓“左”即指东方,所谓“右”即指西方。所谓“陵阳之金”,《汉书·地理志》上云:“丹扬郡:陵阳。”王先谦《补注》:“据《一统志》,今石埭县,汉陵阳地,贵池、铜陵半入陵阳境。”按:铜陵以有铜矿名,即此所谓“陵阳之金”也。我曾链接:《盐铁论》,西汉桓宽编著,记录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集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到京城举行会议,贤良、文学们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反复辩论。《盐铁论》共六十篇,在通有篇中,提及“左陵阳之金”。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三记述了这件事: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顺便提及,金属货币在中国的始用年代,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盐铁论·错币第四》云,“夏后以玄贝”,即指黑色的贝。按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出有铅贝,呈灰黑色,夏纪年时期有铅质的仿制贝是可能的,但不一定作为货币使用。用青铜铸造的币,以及包金的铜贝,在商代晚期即已出现。言归正卷,我曾前往铜陵市博物馆参观学习,铜陵馆藏青铜镜三十多面,时代最早的是一面四山境,为铜陵市井湖集团乔东球先生捐赠。在汉代铜镜上,经常可以见到“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之类铭文,证明丹阳铜在当时人们心中已享有较高的声誉,而丹阳铜的产地就在皖南铜陵一带,所产铜料除用于铸币外,相当一部分输入各地官府作坊制作铜镜。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认为“汉有善铜出丹阳”“新有善铜出丹阳”属于“尚方”镜铭系统。“尚方”是当时中央直属的手工业官署,其铜镜来源大多是丹阳铜铜陵铜矿。我曾经在年代上做了一些考证,铜陵市现有的铜镜,最早的是西汉末新王莽时期,多数铜镜属东汉及以后,均不早于《盐铁论》的“陵阳之金”,也就是说“丹阳铜”之名略晚于《盐铁论》的“陵阳之金”,更晚于屈原的“陵阳之金”。因此,我认为铜陵市立市之铜、铜陵有色公司立企之铜,名称不是“丹阳铜”,而应是“陵阳之金”。
五是太史公南游略而不书陵阳山。我研究屈原,喜欢将司马迁《史记》与司马光《资治通鉴》联系起来读,喜欢将屈原《楚辞》与王琦《李太白全集》联系起来思考。《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或者更后一些。据《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介绍:“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此段话说的很清楚,司马迁是“二十而南游江、淮”的。李白,字太白,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清人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五,有李白的《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序》,其序云:“青阳县南有九子山,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华。按图徵名,无所依据。太史公南巡,略而不书。事绝古老之口,复阙名贤之纪,虽灵仙往复,而赋詠罕闻。予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时访道江、汉,息于夏侯迴之堂,开簷岸帻,坐眺松雪,因与二三子联句,传之将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介绍了屈原“为怀王左徒”、“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等,独没直接介绍屈原放逐陵阳、做铜官的资料。九华山,古称九子山、陵阳山。李白在《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序》中,解释为“太史公南游,略而不书。”不知妥否,也算一说吧。又如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九,有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旧注:五松山,南陵铜坑四五六里。其中诗句云:“千峰夹水向秋浦,五松名山当夏寒,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秋浦,水名,在池州,秋浦县依此水立名。《唐书·地理志》:南陵有铜官冶。《元和郡县志》:铜井山,在南陵县西南八十五里,出铜。《一统志》:铜官山,在铜陵县南十里,又名利国山,山有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铁煮铜,旧尝于此置铜官场。

△苏雪林《屈骚新诂》 资料图片
六是苏雪林认为屈原护送眷属安顿于陵阳。苏雪林(1897—1999),原名梅,字雪林,笔名绿漪、老梅等,安徽太平人。她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是集学者、作家、教授于一身的极少数女作家之一。苏雪林教授的故乡,今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岭下村,距离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陵阳镇,仅十数华里。苏雪林病故后,归葬故乡。苏雪林教授生前,在《屈原与九歌》、《楚骚新诂》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屈原放逐期间来到皖境,从而疏解屈原《哀郢》的秘密,即屈原是在第二次被顷襄王放逐到陵阳的。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苏雪林对岭下村和陵阳镇充满着感情。苏雪林在散文《归途》中写道:民国初年,我在安庆第一女师读书,每至寒暑假,从长江东下至陵阳镇的路线,是先从省会安庆坐轮船到大通,往南渡过40里的童埠湖,抵青阳县城,可选水陆两路抵达陵阳镇。《哀郢》中“淼南渡之焉如”,“当陵阳之焉至兮”,即记这一段沿水路往南的行程,此二句为倒装,说得如此明白。苏雪林力倡“陵阳”地名说,并具体指为陵阳镇。她在《楚骚新诂》中说:这个地名,今日尚在,乃系一镇。笔者乃安徽太平县人,世居山村曰岭下者,距陵阳镇15里,家中购买米面及大件用品,每遣长工用独轮车到陵阳镇装载。地名是不易改的,所以自屈原作赋至今,经历二千数百年,仍是“陵阳”二字。揭示屈原陵阳之行的秘密,是精研楚辞50年后的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苏雪林,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中论述的:顷襄王21年,白起破郢,襄王迁都于陈,在山中已苦挨9年岁月的屈原,闻此消息后,护送眷属安顿于陵阳。屈原不是护送眷属到新迁的陈城,而是最终选择了陵阳。苏雪林虽未进一步言明屈原选中陵阳的原因,但她在《楚骚新诂》中却说:“战国时代,由楚江(长江)至今芜湖境内的青戈江的水路,是便利的,由青戈江到陵阳,依靠舟楫也非常方便。”我为苏雪林教授生前没有提出“屈原放逐陵阳做铜官”而感到惋惜,我也为能与苏雪林教授在天之灵对话而感到庆幸!
(作者简介:钱征,安徽省东至县人。笔名师陵漪、卧牛山人、杏花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池州市屈原学会创会会长。)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